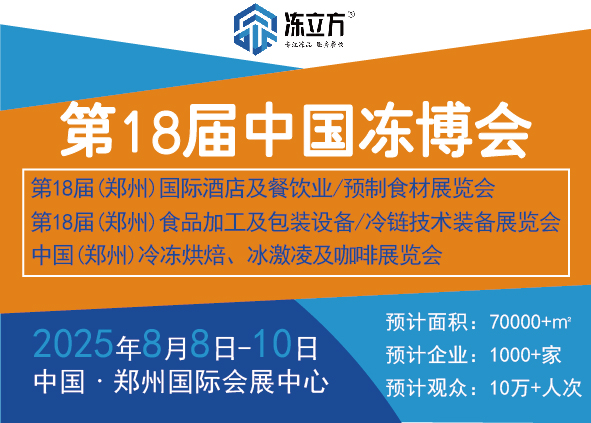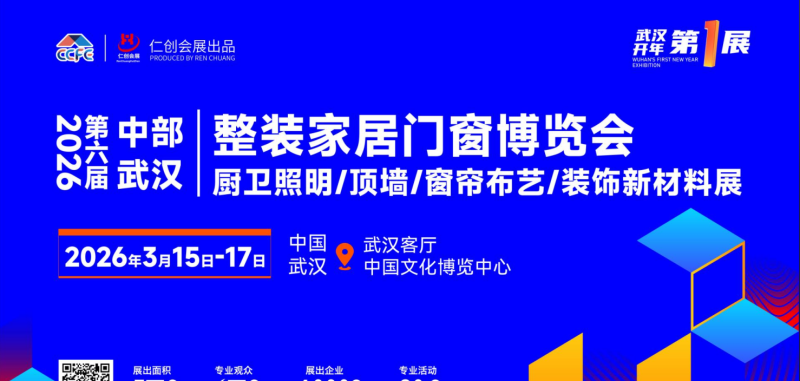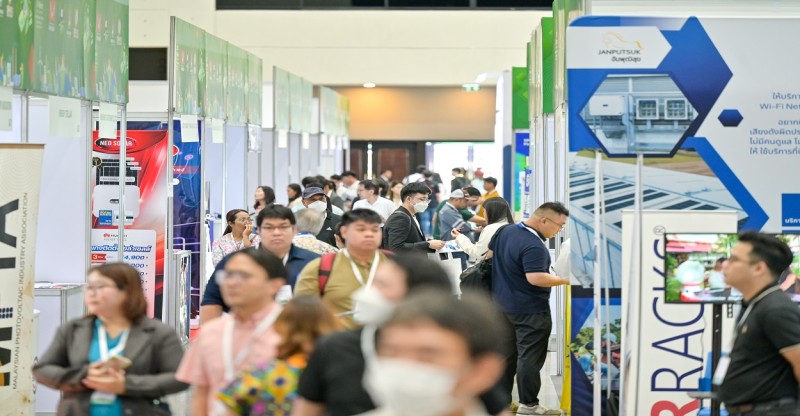编者按:
“外派”群体是在一个特殊时期、内地干部受组织委派、在一个特殊环境工作的一批优秀人才。《外派》这本书的作者外派香港22年,先后担任数家中资金融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从事过银行、保险、信托及上市公司管理工作。本书用记述手法,真人真事描写叙述了作者在港工作的日日夜夜,真实袒露了作者对于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情况的看法、判断及感受。
本书不仅是一本在港员工与外派干部携手合作共同创业的回忆录,也是一本对已逝去的“老外派”缅怀的追思录,更是一本激励新时期港澳外派工作人员的心灵鸡汤。

收人、生活与纪律
我们外派的早期年代,国家经济实力远没有今天强大,故外派人员的收入待遇并不高,对外派人员的纪律约束要比现在严得多,但外派人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比后来的一些人强得多。
我初到香港时,所有外派人员执行的是新华社依据财政部意见制定的工资标准,简单说就是按内部职级套,处长拿处长的钱,厅长拿厅长的钱。记得当时新华社社长许家屯也只能拿3000多港币,我当时为正处级,每月工资也就2300港币左右。根本没有现在的什么市场化、本地化之说。直到今天,我一直认为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市场化是个伪概念,因为高管人员的产生和绩效考核根本没有一整套完全市场化的评价机制。当时的工资标准虽比内地高出十数倍(我在内地月薪为122元人民币),但却不到自己公司名义工资的十分之一,如果和香港人比起来,仅能算低收入人士。那时候到大的商场买点价格高的东西,因讲普通话,常被店员问是不是从台湾来的,每每我都会说是从北京来的。
香港的企业在财务上从来都是公私分明,员工私人开销没人会到公司处理,外派人员的私人电话、应酬等完全由个人自理。我刚到香港时一次因一个干部问题打长途电话给人保吉林省分公司孙若枫副总经理。在谈完正事后,他关切地问了香港的很多情况,诸如天气啊、治安啊、工作环境啊等等。那次电话我是看着表打的,一分钟十几港币,我又不好意思说是自己花钱打电话,真有一种咬牙挺的感觉。一直讲到聊无可聊,最后看时间,半个多小时过去了。下个月电话费单来时一看,400多港币打出去了,一个月工资也开销掉了五分之一。那时一年的收入除去日常开销加上探一次家后几乎所剩无几。有人对此不解,其实那时探一次家就是一次“大出血”,因为一年回去一次,亲朋好友对你从香港回来都有很大期望,一个人买一份100港币的礼品,100个人就要1万港币才能有所交待。记得到香港不久我去看望到港考察的我在省委组织部工作时的副部长张平。他问了我的收入情况后,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省委组织部的年轻人就你最狡猾,一个月挣的比我一年的工资都多!实话说,那时外派人员的生活不好用清贫来形容,但离富裕仍差了十万八千里。一次,一个年轻外派人员准备离港休假回家。走时赶上住宅停水,他没仔细检查水龙头开关就走了。结果他走后不久水来了,一直流了一星期。多亏住在他隔壁的另一个外派干部细心,听到他房间日夜都有流水声感到奇怪,找来备用钥匙打开房门一查看,是水龙头未关,虽然马上关上,但二三千块钱的水费已发生了。这个外派人员为此足足念叨了一年多时间,真是肉疼啊!当时有一个机构的外派人员宿舍被盗,盗贼翻遍了宿舍也找不到一点值钱的东西,最后气得把电视机抱到浴缸里放了水泡上,临走又在一张白纸上写上了“穷表叔”三个字放在茶几上。表叔是那时香港人对我们这些外派人员的戏称。因为京剧《红灯记》里有一句唱词是“我家的表叔数不清”,而戏里的“表叔”指地下党。
当时对外派人员的纪律约束也是很严格的,如夜晚11点前必须归宿,订阅报纸只能订《文汇报》、《大公报》,不准买卖股票,离境必须报告,不准出入红灯区,不得看三级片,等等。连与内地通信也必须通过中国银行的一信使转,即内地的信要寄到中国银行深圳分行交一个叫余苏的转,我们的信也必须通过他寄回内地,可一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这个余苏长啥样,是男是女。好几次的纪律教育我都听过一个故事:一个短期到港工作的内地公职人员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什么心理,跑到电影院看了一场三级片,结果护照落在了电影院里。之后他又去了其他一些地方,待发现护照不见了已是一天以后。按外事纪律他赶紧向新华社报告。当时新华社有关人员让他回忆去了哪些地方,他死活未敢提去过电影院。后来新华社人员提示他有否到过电影院,他无奈地承认去过,但说是看的别的电影。原来电影院工作人员在电影散场后清洁影院时发现了他的护照,因无法联系到他,便把护照通过入境事务处送到了新华社。这个人后来受到了纪律处分。我们集团的一个年轻外派干部因为想家,在一个圣诞节未打招呼就离开了香港。恰巧临时有事要找他,数次打他宿舍电话没人接听,找了一些平时与他联系多的人也不知道他的去向,管理处的领导一下子紧张起来,当时一准备报告新华社,二准备报告总公司,因为真要有一个外派人员跑了,责任谁也承担不起。好在当时的领导还算有担当,反复讨论了他的人品及政治素质,最后决定再等等看。那时真要向上级机关报告的话,这件事一定弄得小不了。最后,节日的最后一天他回到了香港,领导也只是教育了一下就未再追究此事。
因为收入有限,所以像洗衣服、理发这类事我从来不会用外面的服务,每个月头发长了不是我找在中国再保险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的周延礼帮我理,就是他见我头发长了主动约我到他的宿舍去理,有时他还会管一顿饭。洗衣服初期还会用国内的传统办法压平折叠,后来我就提议给每个外派人员宿舍都配置了烫熨衣器具。当时我有一个理念:外派人员的衣着没办法奢侈华贵,但一定要整洁得体。我看到哪个外派人员若穿着未经熨过的衬衣上班,一定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损上几句。一直到今天,我若见到一些穿着未经烫熨衬衫的人,心里总会对他产生另外一种判断。我看到一些外派人员来港后一段时间仍穿着内地带出的衣履,逮着机会就鼓吹穿“名牌”,并经常扬言不买衣服就应把服装费收回。其实当时香港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大品牌店,我所谓的名牌也只是英法国家的普通品牌衣物。对此我有一个理由,就是一个人穿上有品牌的衣服可能自信心都会不同,说到底,外派人员的形象不能太差。当然,我也知道穿品牌和有品味不一定是一回事,但“人靠衣裳马靠鞍”的道理得讲,因为到哪儿都有“先敬罗衫后敬人”的习俗。
依当时外派人员的收入水平,平日没谁有条件能出入一些有档次的消费场所。为了犒劳自己,至多是周末几个人张罗烧几个可口的小菜,弄点啤酒、白酒聚上一次。这个月张三张罗一把,下个月可能会轮到李四。我平素几乎不下厨房,因一个人的饭菜怎么弄都不是滋味,特别是夏天,做一顿饭后一身臭汗,从厨房出来什么都不想吃了,便经常以“君子远庖厨”来自我开解。但不能总蹭人家的饭吃,便在一个周末跑到深圳买了吉林省政府办的天池饭店的熟猪手,回来后又到市场买了新鲜的鱼及其他汤料、蔬菜,用了一下午时间煲好了汤,之后叫来七八个单身在港的外派人员一起蒸好了鱼,做好其他的菜。等汤、鱼、猪手摆上桌时,众人一片欢腾,那时才知什么叫饿底子,没人客气,没人谦让,一会儿工夫汤煲见底,其他的菜肴、两瓶白酒也被众人以风卷残云之势一扫而光。之后还有人嘱咐我以后再请,要多从深圳买些猪蹄子。由人保总公司财务部总经理任上派到香港当管理处副主任的吴小平有喝几口的习惯。他高中毕业就被派到埃及学语言,在英国工作过,后回到总公司,先后任再保险部、财务部总经理等职。他到香港后,我和他开玩笑说他是全面锻炼,之后就等着提拔了。后来,他果真官至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及大型国有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那时我每次去深圳,他都会嘱我为他带回一瓶二锅头,其实也都是为了节省点支出,因香港的白酒要课百分之百的重税。只是后来不知他是否还喝二锅头,估计档次一定是提高了。
一些较长的节假日对单身的外派人员是较难熬的。记得外派第一年的圣诞节,我无处可去,便在放假前买好了假期要吃的东西,之后一个假期再未出门。除了吃饭张张嘴,未和任何人说过一句话。无聊时看看电视,自己的情绪也随着剧情的变化而变化,或微笑或沉默,根本不想理会外面是什么样的节日气氛,也更不想听什么他人的欢声笑语了。那时我有一个感念:意志不坚强的人,担当不了外派人员的角色。
作者简介:
关浣非,博士后,复旦大学专业学位校外导师。1989年1月外派香港,22年间先后任中国保险港澳管理处业务部副总经理、香港民安保险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交通银行香港分行副总经理兼贷审会主席、交通银行信托有限公司董事,在香港及内地创建中国太平洋保险(香港)有限公司、中国交银保险有限公司及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并分别出任行政总裁、董事长等职务。自2011年2月起先后出任香港多家上市公司CEO、荣誉主席、执行董事、独立董事等职。 在香港及内地出版有关银行、保险经营管理、香港经济增长专著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