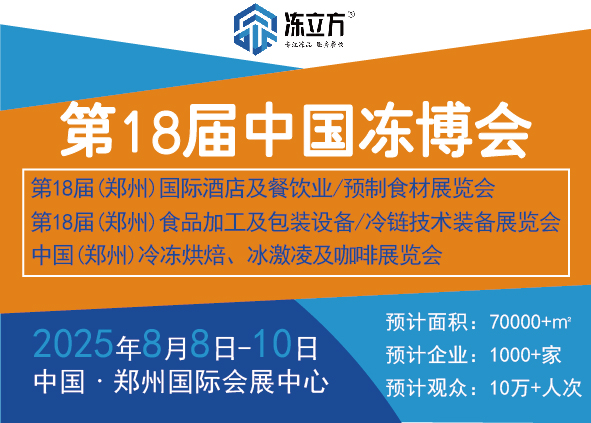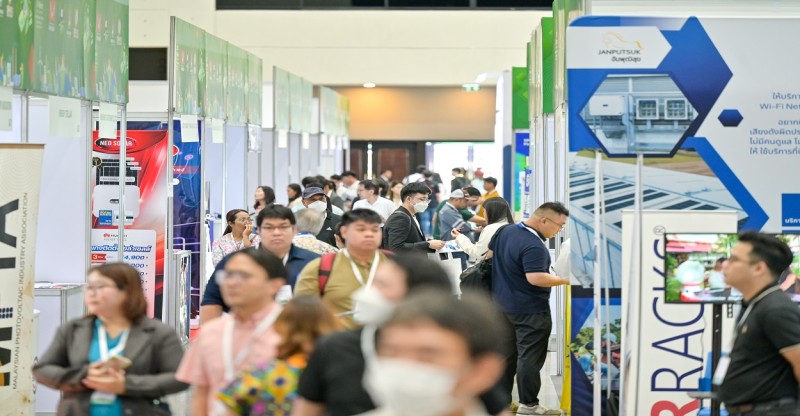医疗卫生从关注疾病转向注重全民健康,是一次重大的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召开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将“健康中国”建设上升为一项中长期国家战略。会后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了建设“健康中国”的大政方针和行动纲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关注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完善国民健康政策,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最近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进一步强调指出,“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加快建立完善制度体系,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实现健康和经济社会良性协调发展。”这对制定我国“十四五”卫生健康发展规划,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为我国卫生健康领域的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的法律,《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于2020年6月1日开始实施,目的在于发展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保障公民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提高公民健康水平,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是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途径,而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建立分级诊疗制度的关键。推动建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主要原因在于传统医疗卫生服务模式的碎片化和医患关系的脆弱化。20世纪80年代,随着赤脚医生形式的瓦解,赤脚医生转变为个体性的乡村医生,乡村医生与农村居民之间的服务关系也演化成商品交换关系,农村居民从此步入漫长的自由择医时代。由于缺乏“健康守门人”制度模式,农村居民一度有病不敢医、有病不会医,不仅导致医疗卫生资源的浪费与医疗费用的攀升,而且导致患者疾病负担的加重与健康生命年的损失,以及医患关系的紧张与恶化。因此,探寻一种既适合中国国情,又科学合理的契约服务关系模式,成为当前学术界和实务界的一项重大关切。201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见》,大力提倡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努力将签约服务扩大到全人群,形成长期稳定的契约服务关系,基本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全覆盖。在此背景下,张奎力教授的著作《家庭医生来了吗?——农村社区医生和居民契约服务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出版,可谓恰逢其时。

张奎力教授长期从事我国医疗卫生制度研究,在农村地区开展了多项基层卫生服务体系的实地调查,积累了不少田野资料。本书是这些调研工作的进一步系统化。全书遵循“建什么—为何建—如何建”的逻辑思路和“理论基础—制度构建—理论构建”的研究框架,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个主题展开探讨。基于社区治理和社会资本理论,本书提出建立农村社区医生和居民契约服务关系的制度模式和关键步骤——“健康守护人”制度,以及建立该制度模式的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多元化的农村基层卫生服务人才队伍建设、以“按人头付费”为主的支付制度改革、以患者为中心的卫生服务纵向协作机制、以社区赋权为核心的社区卫生参与机制。显然,这项研究不仅具有较强的应用和实践价值,而且具有一定的学理性和理论价值。建立农村社区医生和居民契约服务关系,不仅能够有效解决农村居民就医盲目无序流动及由此带来的看病贵、看病难问题,建立健康、稳固和持久的医患关系,而且对于实现医疗卫生服务重心下移和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使新医改能够平稳、可持续地趟过“深水区”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基于扎实的田野调查和长时间的理论积累,作者能够在一些领域提出了前人未发或言之未详的见解和观点。
作者率先提出了“健康守护人”制度模式,突破传统研究单纯关注社区医生的主导作用而忽视发挥农村居民主动性和参与性作用的研究范式,从农村社区医生和居民共同参与、双向互动的层面构建契约服务关系,而且基于西方既有理论与中国社区治理实践之间的巨大张力,提出了社区协商治理理论,认为社区协商治理是展开有效的集体行动进而实现社区善治的关键。这些理论创新尝试既丰富和发展了初级卫生保健理论体系,也为推动社区治理与社会治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健康守护人”制度必须以强有力的激励约束机制来保障。这种激励约束机制具有自愿性、参与性、开放性、竞争性和整体性等特点,与地方性试点的“家庭医生制度”不同,也区别于国外的“守门人”制度。作者认为,这是一种适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新医改进程的制度选择,同时也是一种具有过渡性质的开放式的制度形式。当然,这种管理模式并不能完全契合形态各异的中国农村社区,但适用于部分地区。通过试点,这种制度的利弊优劣可以充分显现,还可以结合新医改其他措施的推进整体上有利于促进人民的健康。
建立农村社区医生和居民共同参与、双向互动的契约服务关系至关重要。传统研究过度关注服务的供给方在制度构建和运行中的主导作用,而相对忽略服务的需求方能动性功能的发挥,把需求方视为一群被动的服务接受者。这种研究范式显然遵循的是“自上而下”的单向输出路径,由于供需双方的错节容易导致制度“春办秋黄”不具有可持续性。本项研究提出,农村居民在契约服务关系中不应是一种被动接受式的状态,而应体现出其主动性和参与性,在制度构建过程“用手投票”表达其愿望吁求,在制度实践过程“用脚投票”表达其选择自由。从这个角度分析农村医疗服务的契约关系,也是卫生研究的新视角,即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起来的研究范式。坚持这种研究范式,不但能够防止服务的制度设计与群众对于服务需求两者之间的偏离,而且可以保证制度的可持续运行和发展,因而是一种值得鼓励和尝试的研究范式。
注重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是本书一大亮点。作者提出了建立完善的社区医生和居民契约服务关系,需要树立“去行政化”的改革新理念。破除行政性垄断并实行“管办分离”、破除不当行政管制并实行“重新管制”,让政府、市场和社会各居其所、相得益彰。当前要实现政府管制职能两个方面的转变,一是从直接经济性医疗卫生管制向间接经济性医疗卫生管制转变,二是从直接经济性医疗卫生管制向社会性医疗卫生管制转变。
当然,书中提出的“健康守护人”制度模式及社区协商治理理论仅是学术层面的一种尝试,它需要走向实践并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作者认为,“健康守护人”制度模式是一种既适合中国国情又科学合理的契约服务关系模式。如果应用于社会生活,将使社区医生真正成为农村居民的“健康守护人”,而不是仅呈现为形式上的“只签不约”,一旦农村居民能够真正从签约服务中受益,那么他们将会由过去“要我签”转变为“我要签”,从而有助于社区医生和居民形成长期稳定的契约服务关系。
以上是通读张奎力教授新书的一些体会和认识,权为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国家治理研究智库副理事长、研究员。本文为《“家庭医生”来了吗?——农村社区医生和居民契约服务关系研究》一书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编辑:宗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