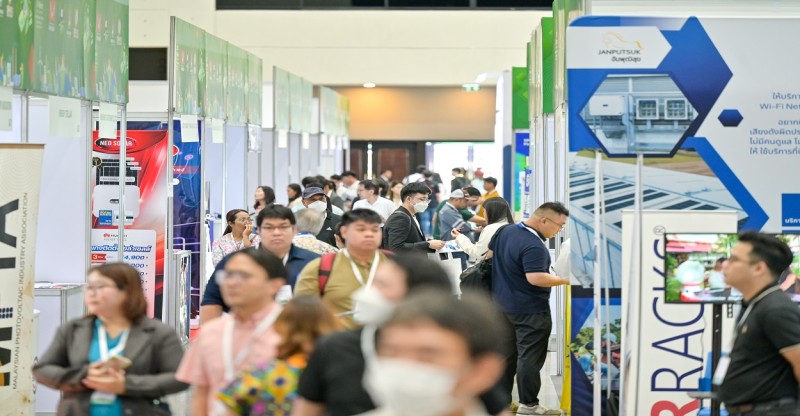第十四节 联中记忆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教育学制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我从四年级升五年级时,遇到了个坎。那时候升级不按学习成绩,就如上大学不用考试兴推荐一样,我留级了。说我年纪小,先让年龄大的孩子上。母亲看见我哭哭啼啼跑回家来,立马就去找了生产队长。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代,生产队长的地位不可小觑,具体细节我无从知晓。后来流传的经典的对话证明了我母亲的聪明和厉害。问:为啥让孩子留级?答:她年纪小。问者:好吧,她爷爷七十多了,你们收吗?答者又说:升级的学生多,学校桌椅不大够用。问者:没关系,我们自带。答者………..,然后我就去联中上学了,竟然没有让我带书桌和板凳。那时十里八村的就一个初级中学,还是在一个四面环水小岛上,巴掌大的小岛上,两排瓦房,前排老师办公用房,后排学生教室,一共有五年级、六年级和七年级,一年级一个班,一个班大约四十名学生。在教室最西头还有一间女生宿舍,宿舍没有床,进门东侧挨墙一溜大通铺,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芦苇和稻草编织的草席,上面铺着花花绿绿的被褥,宿舍只有离家远的学生才能住,家近的都得撑船上学。两排房子的西侧加盖了几间用做厨房,有一个老大爷专门给住校的老师和学生做饭。前排房前,有一块空地做了操场。每天早上和下午我要沿着湖西大堤穿过整个村庄去西渡口码头等我的同学,然后和东渡口的同学汇合一起撑船去学校,有时候因为等同学会迟到。那时候学生迟到会被罚站,在教室外的墙边立着,得站一节课。冬天还行,因为教室里没有任何取暖设施,和室外温度差不多,没风的晴天,墙根底下站着还挺暖和。夏天就受罪了,毒辣的太阳晒得你头晕脑胀。那时家长和老师是一伙的,总是说,没事,老师,这孩子不听话,可劲揍。可能罚站的事家长们也都知道了,而且和我们一起上学的小明哥哥是我们生产队长的大儿子。后来生产队为我们配了船,虽然是一条旧船,大家还是很开心。有一次大风刮跑了我们的船,小明哥哥带着我们顺着运河大堤跑了六七里路才找到。船对于湖里生活的人来说就如人不能没有腿。西渡口一共有六七个人上联中,女孩子两三个吧,那个年代的农村,女孩子大多不上学,上学的大多上个二三年级,顶多小学毕业,升到初中的最多就剩下三分之一。我的两个邻居,和我年龄相仿的大菊和大霞就没上过学,六七岁就在家照看弟弟妹妹,帮助父母做家务,编席子。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农村也没啥生育计划,每家都有一群孩子,三个的都算少的,一般家庭四到六个不等。我的父亲三岁时我奶奶因病去世,解放前还要过饭,解放后十一岁才上了小学,后来农校毕业,有了工作。知道知识能改变命运,四个孩子都让上学。我智商不高,但学习认真,一年级就能教三年级的拼音,升了联中,成绩还可以。虽然要去撑船上学,冬天湖水结了冰还要沿冰凌去。除了那次掉河里差点淹死,沿冰凌也差点漏湖里。刚入冬,湖面结了薄冰,船可以破开。等到隆冬,零下十几度,湖就冰封了,我们就沿冰上下学了。大家一起沿着厚厚的冰面,结伴而行,北风呼呼,吹得孩子们如同湖里那些未来得及收割的芦苇一样东倒西歪。大家依旧嬉笑打闹,男孩子们有的把折断的芦苇当马骑,口里驾个不停,有的手握一把芦苇,不停地摇着,毛茸茸的芦花如同一面面战旗迎风飘扬,同志们!为了革命的胜利,前进!前进!我高兴的手舞足蹈,倒着走的正起劲,突然一只脚踩进了冰窟窿里。其实冰窟窿已经又结了冰,只不过冰比较薄。好在冰窟窿不大,我又穿着臃肿的棉衣,一只腿卡在冰面,我吓得哇哇大叫。大家七手八脚的把我拽出来,笑的前仰后合。我拖着一条湿漉漉的沉重的腿,踩着冰凉的棉鞋,心里恶狠狠地骂着那个未曾谋面就想害死我的砸冰窟窿逮鱼的人,回到家里又挨了母亲的一顿训,还说不久前一个小孩掉进冰窟窿里找不到,不知漂哪里去了。我极度恐惧,不久便背着装满了大米的军绿书包,带着一瓶子咸菜乖乖的去住校了。每个星期回家一趟。有时下雨下雪或大风,住校的同学就会多些,女生宿舍里大通铺上挤满了人,仍旧有同学没地方住。老师不知从哪里弄了一只带蓬的旧船,舱门木头都沤烂了,四处通风散气,我们把船湾在岸边,又合力往岸上推了推,以防夜间漂走。采扁一根芦苇把仓门系上,年龄大的同学在船仓里铺了些芦苇,又在上面铺上褥子,四五个女孩子横躺在狭小的船仓里,蜷着腿,竟然睡得着。睡到半夜,我感觉身子底下凉凉的,大家也都被凉醒了,伸手去摸,褥子已经湿了,原来船仓渗水了,浸透了芦苇,又浸湿了褥子,大家爬出船仓,坐在船头,清冷的月光照在冰凉的湖面,几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拥在一起,不知道坐了多久才熬到了天亮。
自拍红豆与腊梅